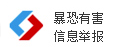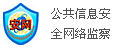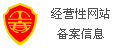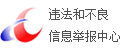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俞墨出国前做的最后一件事,是拜祭她的前夫江适远。
江适远葬在郊外,开车差不多一个小时,弯弯绕绕,要穿行好几段山路。
不是节假日,墓园子里一个人没有,一片萧瑟清冷,在深秋午后略显阴森诡异。
倒不失为倾吐心事的好地方。
她穿过一排又一排的墓碑,找到镶刻江适远照片的白玉石,放下鲜花,静静注视那么一会,随即坐了下来,掏出包里早准备好的酒杯和白酒。
“敬你啊,你生前藏的酒,我替你喝了。”
她举起杯,对着空气碰了碰,一饮而尽。
53°的高粱酒,火辣辣地呛喉,她直到现在也想不通,这玩意有什么好喝的,为什么江适远生前这么着迷,动不动就喝得酩酊大醉,甚至不惜为此跟她争吵。
那几年真是吵过无数的架。
江适远这个人嘛,心眼子倒不坏,就是自私,惜命惜力半点不为家庭考虑的自私。
贪玩,一周七天至少有五天在外面喝酒。三十老几的人了,穿一身花不溜丢的潮牌,跟十几二十的小年轻混一起,哪热闹往哪挤,唱歌蹦迪喝酒玩色子,无欢不作。
家务事半点不沾,出门靠朋友,在家靠老婆,老婆跑了还有旱涝保收拿退休金的爹妈。
不仅是家中独子,还是老来得子,双层叠buff注定他娇生惯养的一生,二老恨不得手心捧着嘴里含着,自然而然养成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性子。
当初这门婚事,俞爸俞妈就坚决不同意。
这得追溯到江适远第一次上门了。
好巧不巧,刚坐下不久,俞墨家的金鱼缸爆了,玻璃炸了一地,水流得满屋子都是,地上还躺着几条垂死挣扎的金鱼,一片狼藉。
俞妈在厨房弄饭,俞爸去买盐了。
俞墨说:“江适远你帮个忙,把玻璃片扫一扫。”
江适远两眼一瞥,没动身,过了老久才说:“你去呗,我怕扎伤手。”
俞墨心想,你怕扎伤,我就不怕扎伤吗?可毕竟当着父母亲的面,怕影响老人家对江适远的看法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为免节外生枝,默不作声拿起扫把收拾起来。
换了别的男人多少有些不好意思,江适远完全没这个压力,这就是他从小到大理所当然的生存方式,什么事都有别人包干,他只要坐着就行。
但哪段美满婚姻里容得下一个干坐着的男人呢?
俞墨去阳台拿拖把时,俞妈妈把她叫住了:“这玻璃多锋利啊,小江也不知道搭把手?”
俞墨讪笑,支支吾吾地解释道:“他在家就这样,不太会做家务。”
现在想想,俞墨那时候是真的很爱很爱江适远吧。
苦也要爱,累也要爱,明知不合适也就想在一起。
年轻人嘛,总有头脑发烧的那几年,不把一腔热血烧成灰是不会罢休的。
可俞妈妈不年轻了,仅凭那一面,她就认定这小伙子绝非良配。
事实的确不出所料。
结婚几年,余墨流过的眼泪,比从前二十几年加起来还多。
江适远什么都不管,张嘴吃饭,伸手要钱,钱花完了就找爹妈要,没皮又没脸,连一个男人最基本的羞耻心都没有。

衣服要穿时髦的,鞋子要买限量款,iPhone每到上新就换一台,花呗白条借了一大堆,爹妈费尽力气给安排的工作,别人挤破头都进不去,他倒好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升职完全无望。
如果世上有后悔药,就是用刀子架俞墨身上,她也决计不嫁他。
偏偏没有后悔药嘛。有的只是年轻人撞破南墙誓不还的决心。她,俞墨,一个知书达理温柔贤淑的名校女硕士,偏偏就嫁给了这么一个胸无大志自私懒惰的小白脸。
|


 主页 > 另类小说 >
主页 > 另类小说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