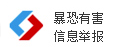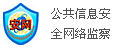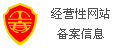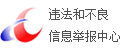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细较起来,倒也不单单是恋爱脑。
俞墨嫁给江适远,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——她有先天性心脏病,心室闭合不完全。
这病吧,说小不小,说大不大,至少目前还没到影响生活的地步,真恶化了,也可以通过手术修复。怪就怪俞父俞母爱女心切,打小开始,时时在孩子面前念叨着这病。
今天愁眉,明天叹气,给小俞墨留下一种极深的心理暗示,即自己得的是个绝症,这辈子都要遭人嫌弃,去哪儿都是个累赘。
从小就为此自卑不已,到了青春期更是心虚谨慎,早在江适远之前交过两个男朋友,还没确定关系,就早早地跟对方透了底。
对方当然说不介意,俞墨却总隐隐不信。
虽然最后分手跟这事没啥关系,可俞墨觉得有关系啊,自卑者都擅长瞎琢磨,不管两件事多风马牛不相及,总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力,把它们强行拽到一起,绕到自己痛处来。
总之,因为这些弯弯绕绕,俞墨对待两性关系自卑极了。
江适远那万事随缘、得过且过、没头没脑的性格,于这事上歪打正着拯救了她。
俞墨说:“我身体不好。”
江适远说:“没事,男性平均寿命比女性短,搞不好我先死了。”
俞墨说:“万一恶化了,连孩子都不能要的。”
江适远说:“要那玩意干嘛,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!”
俞墨说:“现在这么说,过几年就后悔了。”
江适远说:“放心吧,我永远不变。”
如今再看这几句话,桩桩件件,江适远倒真没撒谎,他的确先她而去,他也的确没打算要孩子,他甚至压根没有变过,至死都是少年时不懂事的心性。
字字句句都没骗人,可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他不要孩子,不是担心俞墨的身体,而是单纯不想当爹,不想负责,不想承担家庭的责任。
可俞墨想当妈。这也是她的心魔之一。
因为打小知道自己有病,打小听父母念叨怕她以后不能生育,她就对生孩子这事有种离奇的执念,越怕什么越想什么,恨不得立马延续基因,在有朝一日病情恶化之前,赶紧把生命传承下去。
这种小女儿心事,当然不能指望没心没肺的江适远能感同身受。
就像他说那样,自己还是个孩子呢,要个孩子来干嘛?
为这事俩人也吵。
俞墨说:“你就不能成全我做母亲的心愿吗?”
江适远说:“那你就不能成全我不想做父亲的心愿吗?”
俞墨说:“你现在不想做,以后想做了,就还有得选,可我是没得选的。”
江适远说:“怎么没得选,现在明星不都去冻卵吗?你也去啊。”
话说到这里就到头了,一生没怎么说过脏话的俞墨,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:“江适远,你混蛋。”
所以说这世上的事吧,就是这么错综离奇。
当初因什么爱上他,后来就因什么恨上他,后来的恨是真的,当初的爱也是真的。
她永远不会忘记,当年江适远捧着花单膝跪地跟她求婚时,内心涌过怎样澎湃的爱慕和感激。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礼拜六。
他约她去长隆玩。过山车、跳楼机、大摆锤、海盗船轮番玩遍,嗓子叫哑了,心跳加速了,胃里搅得七荤八素的时候,他突然从人偶身后掏出鲜花和戒指,跪地道:
“墨墨,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,你的温柔,你的善良,你的美丽,你的自律,你的脆弱,你的每一个样子我都喜欢。”
“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,但请相信我,这些都不能成为阻止我走向你的理由,如果以后没有孩子,我们就是彼此的孩子……”
“墨墨,嫁给我,好吗?”
冷风吹过,墓碑前的俞墨猛地打了个寒颤。
她以为自己早忘了,可此时此刻,回忆偏偏如斯清晰,就连当天的阳光都恍如近在眼前,毛绒绒的,晾晒在皮肤上。
那是他们最最相爱的时刻。

那一年,她27岁,他28岁。
今年,她已然37岁,他呢,永远躺在黑暗的地底,冰冷的白玉石上写着他的生年,倘或他还活着,今年也已38岁了。
|


 主页 > 另类小说 >
主页 > 另类小说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