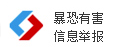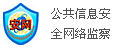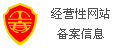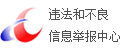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江适远死了。
死得如此冤枉。本不关他事的。本不至于斯的。
一场普通的斗殴,一块小小的玻璃碎片,偏生他管了闲事,偏生就扎进了大动脉。
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,瞪大了眼,嘴巴还微微张着,似有什么话要说,然则一个字都没吐出来,就断然咽下了气,在俞墨眼皮子底下。
那画面一度成为她的噩梦。
此后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,只要一闭上眼,她就看到江适远倒在血泊里的样子。
他的眼睛瞪得那样大,有痛楚,有不甘,有抱憾,他好像想叫她,徒劳地仰着脖子,嘴唇翁动,他想说什么呢?是叫痛吗?那么自私怯懦连金鱼缸都怕扎手的人,应该很怕痛吧!
又或者想叫屈,本不关他事的,他怎么偏偏管这个闲事,关他什么事啊,她俞墨是生是死关他什么事,江适远,你为什么偏要管这个闲事,这下可怎么办,这笔账该怎么算?她欠他的该怎么还?可明明是他伤害了她,怎么倒把她置于迫害者的位置?
江父江母恨毒了她。他们在灵堂里扇她耳光,把她撞倒在地:“都是你,都是你害的,我们家到底哪里对不住你,你要把他害死?”
她就生生地受着。疼痛清楚地袭来,身上哪哪都疼,江妈妈揪住她的头发,一掌一掌朝她挥去。也好,也好,这样一来,欠他的是不是就少了点?
“江适远,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,很讨厌很讨厌,谁叫你帮我了?谁叫你帮我了?”俞墨又倒了一杯酒,倾倒在地:“值得吗?你躺在这里值得吗?你那年才36岁吧,你该活着的,该活着的……”
俞墨的嗓子被糊住了,渐渐一个字都说不出。
他该活着的,他偏偏死了,他死了,他们之间的账就永远算不清了。
是恨吗?是爱吗?是亏欠?是遗憾?早说不清了。
过往种种连着皮带着肉,早跟躯体长在一起剥离不开了,还拿什么来清算?
人这辈子欠什么都别欠人情债,更何况,她欠的不是人情债,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。
甚至有那么几个瞬间,她恨不得躺在地底的是她自己——她实在不想欠他的。
她可太害怕了,万一真有来生,她是不是还得遇见他,还得再还一次债?一想到下辈子还得遇见他,那可真不寒而栗,老天爷不带这么捉弄人。
那么他呢?假使时光倒流,他还会挺身而出吗?他后悔了吗?他会怨恨吗?
她突然想起一些久远的早被遗忘的事。
好久好久久到好像上个世纪的事了。
那时他们刚结婚,有一回,俞墨崴了脚下不来床,江适远就负责洗衣做饭照顾她的起居。他原来也会做饭的,好吃不好吃是一回事,至少饭菜能下口。
她调侃他:“没看出来啊,江适远你会做饭啊?”
他一边往她嘴里送饭,一边油嘴滑舌:“那可不,哪有我江小爷不会的?”
那时候他的确无所不能的样子,至少在她看来是的。
他会弹吉他,会手风琴,还会一点近景魔术,往哪儿一站,哪儿就是联欢晚会。他给她徒手变过玫瑰,让她从扑克牌里随便挑一张,又再从扑克牌中找出这一张:“梅花K,对吗?”
后来她才知道,那一副扑克牌,张张都是梅花K。
魔术是假的,笑容却是真的。
跟他在一起这几年,大抵算作人生最不幸的几年,可也曾是人生最高兴的时光。
他也曾接过她下班,在滂沱的大雨天,从驾驶座上拿着伞下来,一路将她送进副驾座。也曾送过贴心的礼物,是费了好大心思收集的一套绝版邮票,她就这么点爱好,难为他记住了。
有一次他跟同事出差,大半夜非要和她开视频,就这样对着视频睡着了,后来他告诉她,那一夜隔壁的同事找了小姐,他不想这样,他想做个清白的人,就想干干净净跟她在一起。
他的确没什么不干净的。虽则爱喝酒爱蹦迪爱跟狐朋狗友混一块儿,手机却从来都是任她检查任她查岗,即便喝得酩酊大醉,也总要回家睡觉。
可是,回家睡觉的,就是好丈夫吗?
她痛苦极了,痛苦得恨不得把他从地底里揪出来痛骂一顿。为什么,为什么,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?但凡他再好一些,她对他的怀念也能理直气壮一些。
实在不行,他再坏一些也行啊,但凡吃喝嫖赌样样俱全,她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痛苦,爱也不能爱,恨也不能恨,一腔怒气甚至不知该向谁发泄。
大概这世上的婚姻注定磨难。像两团毛线球,往洗衣机里一扔,线头连着线头,线圈揪着线圈,蝴蝶结,十字结,死结,直到凌乱不堪的一团,再也理不出一丝头绪。
理不清了,这辈子都理不清了。
深秋寒了,俞墨裹了裹外套,把自己包得更紧实了。
“这次出国,大概就不回来了,你在底下照顾好自己,少喝点酒,别跟人打架了,怪疼的。”
她把喝完的酒瓶重新放进包里:“要是在外面遇到合适的人,我就再嫁了,你知道的,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孩子,做一回母亲。”
她早想好了,花这么大气力离婚,又花这么大气力活下来,当然得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好好活一次。

这次她会长点心的,找一个好一点的,不自私,不喝酒,不爱玩的,好好地组建家庭,好好地生儿育女,好好地把她从阎王那里换回来的命,传承下去,开枝散叶。
“别再管我的闲事了,如果真有鬼魂,可别漂洋过海来找我了,怪渗人的。”她说了个很冷的冷笑话,嘴唇还未来得及颤动,笑就冷下来了。
随即,她又加了一句,用几乎不可听闻的声音。
“这辈子别相见了,下辈子吧,欠你的,下辈子我都还给你。”
|


 主页 > 另类小说 >
主页 > 另类小说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