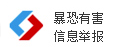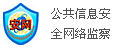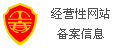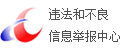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“滚蛋,青蛋子……你的脚后跟踩着俺的鞋子啦,瞅瞅,瞅瞅,俺都穿不上了……”顾庆坤嘴里一边骂骂咧咧,他一边把他蹲在凳子上的大长腿伸下来狠狠踢了旁边的小青年一脚。
就在这个时候,从门洞子外面走进一个矮矮墩墩的汉子,这个汉子一脸坏相,五十多岁的年数,水桶般的腰身,还多了一个大肚腩;他一脸黑着,青色的黑,真实的从他心脏血液里流出的黑,染黑了他的肌肤;两个大肿眼泡子,抬不动的眼角,像极了鳄鱼;一张撅着的吹风嘴,被他的前门牙支撑着,措辞带刀,刀刀阴险;尖窄的下巴上一撮灰色的胡子,跟着他的话音不断地起伏着,那一起一落,不知埋藏着几多阴谋企图?他长袍短衫,全身上上下下没有一个补丁,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处所还能透出不少的亮色,那是上等绸缎做的衣服;他右手握着一把枪,这是他自满的象征,这是日本人送给他的。
他的眼角狂妄地扫过屋顶,他走路一脚左,一脚右,拽着他横着的膀子,他一张嘴,“你们在说什么呢?”一口黄牙,有两颗是金的。
顾庆坤匆匆从他蹲着的凳子上跳到地上,迎着笑脸,“张爷,欠盛情思,俺在吹牛,吹俺的老本行!”
监工姓张,他出生那天,他家里正为他小叔搭喜蓬,他火烧眉毛地、提前一个月来到了这个世上,他怙恃直接给他取名张喜蓬。这个张喜蓬真是多余来到这个世界,他除了心狠手辣,就是嚣张跋扈,更会舔日本人的屁股。
“是吗?没有人骂俺?”
“没,俺虎皮措辞您还不信?俺吹牛的短处没跑……”
“是吗?”张喜蓬把他贼溜溜的眼珠子狠歹歹盯在顾庆坤的脸上,“虎皮呀,不是因为你弟弟在日本学校当教员,哈哈,你是知道的,咱们只有这根绳子的牵强硬套的干系,对付你,俺只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不要给你脸,你不要脸,假如然的落入俺的手里,俺手也不会颤抖一下,俺就是这个性情。”
“俺大白,大白,俺知道您的好,您的照顾全记在俺心里了,对,今儿正是时机,您随意,这酒钱记俺虎皮的账面上,来,来,您请坐!”
“哼!今儿,俺没时光,日本皇军让俺下来巡逻,看看哪个不长眼的能撞到俺的枪口上?”张喜蓬一边吹胡子怒视,他一边举起他手里的手枪在他细细的鼻尖上晃了晃,“看到了吗?这个死得痛快,但是,日本人,不,是俺更想看着没有腿、没有手的在俺面前扭动……”
酒馆里的人一看到张喜蓬就阉了,又听到他嘴里一席话,只吓得全身筛糠。
谁人方才抱怨监工的小青年吓得全身打颤,他的身体歪斜在酒桌上,假如没有酒桌支撑着他,他大概已经瘫在地上了。顾庆坤匆匆用他清瘦的身体把谁人小青年挡在他的身后,他依然陪着笑脸,“就是,张爷,您就是咱们矿工的最大头领,您的话就是圣旨,有哪个敢不听?您只要有什么指使,俺虎皮宁肯唯首是瞻!您需要俺做什么?您尽量叮咛,除了杀人,俺杀猪杀虎不在话下,手不颤抖!”
“好,虎皮呀,有事俺再找你,你也给俺盯着这一些贱货……”张喜蓬一边说,一边扭转他肥胖的身体走了……
酒馆一下沉寂了,谁的心跳也能听到,薄薄的胸膛与心脏只隔着一层皮。
虎皮的额头在冒汗,他抬起衣袖擦擦汗珠子,他逐步退着身体,逐步把他窄窄的屁股放在了他身后的凳子上。
少顷,酒桌上冒出一句两句,全是唉声叹气。
“吆,今儿我们的虎皮嘴巴挺顺溜!”一个身穿旗袍的姑娘从酒馆后堂走了出来,她脚上一双高跟皮鞋,看着像是在脚上绑上了一节高跷。
酒馆的汉子们抬起了眼角,他们呆头呆脑。
这是一个很是尽善尽美的面目,一双细细的眉眼,像唱戏的戏子,更像狐仙;皙白的肌肤,嫩嫩的、细细的、粉粉的、伸手掐掐能出水,出水的芙蓉;鹅蛋脸型,不窄不宽,那么符合,鼻挺嘴小,相得益彰。
顾庆坤一抬眼,两小我私家眼光相撞。
顾庆坤一激灵,她怎么来了?
来人是谁?跟顾庆坤又是什么干系呢?
来人是顾小敏的二姨,也是顾庆坤媳妇的妹妹。名字乔丹霞,本年方才二十三岁。
“你……”
“奥,俺还没先容一下本身,俺是何处……”姑娘嘴里娇滴滴的、笑盈盈的话堵住了顾庆坤的嘴巴。
她抬起细细的胳膊,伸出纤纤玉手指指酒馆对过的红屋子,“俺是那儿的,俺来了一个多月了,俺叫玉香儿,故乡是德州的,今后在这儿讨口各人的剩饭吃,但愿各人伙儿多多恭维啊!”
|


 主页 > 另类小说 >
主页 > 另类小说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