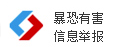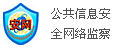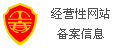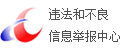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本日他的姑娘又给他生下了第三个丫头,他苦闷,他沮丧,他想生机,他的火已经守着接生婆方才向他的姑娘发过了,此刻他只想用酒精灭一灭心里的余火,越喝火越旺。
听着屋里孩子的哭声,汉子想起了三年前,因为他二女儿的出生,他一狠心把他两岁的大女儿送了人,送给了住在坊茨小镇上的一对德国老人,他们没有子女。他曾偷偷去看过,那对德国伉俪对他的女儿挺好,无论住得、吃得、照旧用的,都比随着他强,不是一星点的强,是翻天地覆地强,他欣慰,他有点自得,他的嘴角竟然暴露一丝笑。抓住酒壶往嘴里再倒一口酒,“他妈的,真苦!”他嘴里骂骂咧咧,不知他说酒苦?照旧说他的糊口苦?
屋里的姑娘不知又想起了什么,她也许想起了更多的悲痛事,开始嘤嘤哭啼,泪水在她脸上纷至沓来。她一边哭泣着,她一边用爱怜的眼神看看方才来到这个世上的小女儿,越看、越想、越难熬,她不敢大哭,她只能偷偷地、掐着喉咙,她真的很难熬,憋不住了,泪水浇湿了她洁白的前胸,滴落在怀里嘬奶的婴儿的脸上,可怜的孩子呀,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?你来受苦呀,这世上的苦你的母亲已经吃够了。
这个姑娘二十多岁的年数,容貌虽不尽善尽美,也算的上清秀,一双悦目标丹凤眼,黯然伤神;五官菱角理解,那是瘦的样子;肌肤不黑,却带着黄色,尚有疲劳,更多的是虚弱;像草一般的头发垂在她的胸前,荡在婴儿的脸上。
“臭娘们,哭什么哭,尚有脸哭,你有才干生个儿子出来?你觉得你老爷们好措辞吗?瞅瞅你,又挥霍了俺一壶酒钱……”
在不远处的一条泥泞不堪的羊肠小道上走着一个老妇人,老妇人蹍着一双三寸金莲,一摇一晃。
路旁是一家连着一家的矿工家眷院,有的就是一个篱笆院,有的还能立起一个门洞子,有的甚至没有院子,直接进屋上炕……
这个老妇人每走一步就停下来长长地喘口吻。看着岁数不太大,五十岁阁下的年数,不宽不窄的脸庞,高鼻龙眼,五官挂着点男相;脑后一个灰白色的髽髻梳得油亮,高高的额头上挂着愁云惨雾,好像有许很多多的烦恼搅得她心神不安,喘息都不顺;一身旧棉布偏襟短袍,一条肥大的水桶裤缠着裤脚,尚有一件无袖碎花坎肩套在短袍的外面。从她一身行头看,就知道她的日子不算太差。
她抬起昏黄的、满是皱纹的双眼,环视一圈附近,再掂掂手里的两个铜板,她嘴角往外扯了扯,暴露一点点笑容貌。
这个老妇人姓夏,她就是这一带的接生婆。她方才顺利地完成了一件差事,又顺利获得了两枚铜板。
她一边继承往前走着,她的眼角一边迅速地扫视着阁下,不知道她在寻觅什么?是谁家不小心丢掉的一件衣服?照旧一块窝头?这个时候家家户户没有衣服穿,更吃不饱饭,她只醒目想;她的耳朵支棱着,猜疑是她的职业病,她想听听哪家的婆姨该生了,她又可以赚几枚铜板……举起手里的铜板在面前晃晃,她名誉她本身有这个手艺,多几几何、时不时地有进项,可能几斤粗粮,她都很满意;她嘴角撇着,她早已经听到了她身后谁人酒醉汉子的吼叫,她匆匆把手里几个铜板使劲揣进了怀里。
这儿是一个杂居区,根基上没有当地人,镇上的人口除汉族外,尚有回、满、蒙等少数民族。顾家是这儿独一的异性。
这个满嘴酒话的汉子就是这儿独一顾姓。
汉子身边的泥地里坐着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幼儿,差不多两岁多点。满脸脏兮兮的,鼻涕与口水黏满了前襟,偶然仰起脸,下巴颏上一片湿疹,一个个红红的疙瘩泡在鼻涕与泪水里。她时不时抬起张煌的小眼神看着她身旁喝酒的汉子,她好像还不怎么会措辞,但,她已经有了痒的感受。
见汉子没有答理她,她嘟囔着小嘴垂下头去,一只手抓着地上脏兮兮的土壤玩耍,另一只小手一个劲地挠着下巴颏上的湿疹,可怜的娃娃本身挠疼了本身,开始“哇哇”大哭。
“哭,哭,哭死你!”“啪”汉子一边向女孩吼着,他一边把手里的空酒壶摔在他旁边的墙上,传来清脆又逆耳刺耳的声音,四溅的玻璃碴瞬间蹦起。有一块玻璃碴溘然飞起穿过了女孩的耳朵。女孩一声尖叫划破了沉闷的氛围,接着就是大哭。
听到孩子凄厉的哭声,接生婆溘然停下了脚步,她逐步扭脸往身后瞟了一眼。
只见谁人汉子溘然跳起身来,伸出一双大手抓起地上的女孩。
女孩的右耳朵被溅起的玻璃碴子割伤了,一个肉嫩嫩的小耳朵唇豁了一个大口子,血水正从女孩的脸上顺着脖子滴下来。
“虎皮呀,这孩子,这孩子耳朵要掉了!破相了!”
接生婆的声音吓了汉子一跳,他猛地扭转脸,他的双目瞪得像灯胆,他没说一句话。
“这孩子,你不想要,就送给俺,俺不嫌弃!俺归去给她缝几针,丑点丑点,只要不缺就行!您看行不可?”
“你,你什么意思?”汉子张口结舌。
“你家的姑娘不是又给你生了一个小丫头吗,这个给俺,你们小两口再生一个……嘿嘿……虎皮,你可快点拿主意呀,这个孩子的血快淌没了!”
“不可,不可,我的孩子,我的女儿……”坐在房子炕上的姑娘坐不住了,她衣衫不整的、丢魂失魄地扑了出来。
|


 主页 > 另类小说 >
主页 > 另类小说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