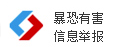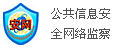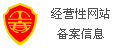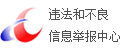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朕从前就以为谭嫂子是个贤惠有打定的女子,公然不错。第一个给子女报名,未来他们成才,全都是你佳偶的功勋。谭年迈更有远见,竟不重男轻女,未来享福的日子在背面呢。”
谭嫂子汉子原来还因为女皇夸媳妇没夸本身不自在呢,谁知月皇给他的评价更高,笑得合不拢嘴,谦虚说“做爹娘的都巴望着子女好,这有什么”云云。
李菡瑶微笑道:“这就很不容易了,这世上,并不是所有的爹娘都如你们这般想。”
谭嫂子如遇知音,拍腿笑道:“可不是!有那样人家,亲生的女儿都作践,比捡来的都不如;不是亲生的就更不像样了,比畜生都不如。就说我们那条街上有一家——”她措辞时左顾右盼,一扭头瞥见聿真,即刻想起他适才问本身的问题,原来本身要回的,因忍不住嘴痒接了月皇的话,把他丢在一边不理了,这欠好,忙话头一转,歉意道——“令郎问里边为什么吵吵。是魏夫子,说学生要住在书院,十日一休。有人就不乐意了,说她女儿晚上要回家喂猪;尚有人说她女儿要煮饭洗衣裳、伺候婆婆,她那女儿才六岁……”
周围人愣了下,一阵唏嘘。
只有李菡瑶见责不怪。
聿真笑问:“那大嫂和年迈怎没吵?”
谭嫂子大声道:“吵什么!有什么可吵吵的?月皇花那么多银子在娃儿身上,难不成是银子多了没处使?”
不等人回,她本身答道:“那是为了教孩子成才!住在书院才好呢,管教严厉些,娃儿们也不敢偷懒,否则白日学几个字,晚上一撂手,回头就忘光了。那婆娘眼皮子浅,一头心思巴望着她家丫头给她挣月银和米粮,一头心思又想着等这丫头放学回家干这干那,上学做家务两不延长。想两端都顾着,只顾贪心,也不怕未来什么都捞不着!”
聿真赞道:“照旧大嫂想得大白。”
月皇笑吟吟道:“朕就说嫂子是大白人。”
谭嫂子得了夸赞,喜得合不拢嘴,把她一双子女往前一推,教导道:“你俩给我记好了:进去要用功。家内里,娘和你们爹辛苦些,只要你们争气,再苦再累我们也宁肯。也不指望你们能像鄢相和落相那般前程——他们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,比不了——娘只要你们能认得几个字,能写会算,未来立室立业,不做睁眼瞎就行。”
这话看似说给孩子听的,其实说给周围人听的。
两个孩子虽怕羞,却信心十足地承诺了。
谭嫂子俭朴的愿望,令人另眼相看。
孔夫子和何陋对视一眼,都以为脸色极重。
孔夫子轻笑道:“老汉或许大白了,月皇想用三年的时光,造就一批人济急,故而令学生住在书院,严加管教。然,‘一年之计,莫如树谷;十年之计,莫如树木;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。’三年的时间,够做什么?”
何陋也笑道:“月皇天纵奇才,李家大富,江南王满腹经纶,还请了不知几多名师,天资、物资和师资集于一身,成绩本日的才学,也不止三年罢?”
周昌接道:“正是。贩子黎民,糊口艰巨,不愿让子女住在书院,也是不得已,但愿他们能帮家里一把。月皇迫令他们住在书院,眼下他们贪图小利,或可遵循,三年后呢?没了这丰盛的优待,能留下几人?”
李菡瑶笑吟吟道:“诸位说的都在理。但朕行事:从不落无用之棋子,不做赔钱的交易,不打无筹备的战役。本日能留下他们,三年后虽然也能留下他们,甚至吸引更多的孩子来上学念书,尤其是女孩儿。”
周昌忙问:“如何留下他们?”
李菡瑶神秘道:“这个,无可见告。三年后自知。”
黄修瞅了周昌一眼,“汇报你了,你们好归去想对策,嫡再来使企图?你好大的脸!”
周昌气道:“谁使企图了?”
黄修道:“不使企图你们来做什么的?一个个饱读诗书,却在这大放厥词,阻人送女入学,手段下流!”


周昌抖着手指他,“你……你这老匹夫!你又好到那边去?你原先不也阻挡月皇,发明她是你门生,你才有了私心,墙头草似的,又改为支持她了。”
黄修道:“老汉那都是被你们蒙骗的。”
两人吵了起来。
李菡瑶忙劝止,不给他们辩白的时机,大声叫:“听琴。”
周昌黄修不知她要做什么,忙住了嘴。
听琴道:“在。”
李菡瑶道:“你去跑一趟。”
听琴道:“是。”
|


 主页 > 另类小说 >
主页 > 另类小说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