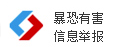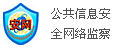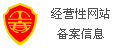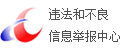这是每个女性都希望回避的话题,宁可谈谈诗歌,说说烹饪,哪怕扯扯中美贸易战争。有过被性侵经历的,就更是躲着这个话题走,哪怕提到性侵这个词儿,那个场面就会回来。
最大的伤害,就是那一刻会回来。非常清晰,当时的季节,白天还是晚上,是晴天还是阴天,当时穿什么衣服……哪怕10年之后,一切都非常清晰,好像昨天发生一样,而情绪呢,也如昨天刚刚被强奸。
场面不断回来,是遭受性侵者普遍现象,那副画面随时出现,哪怕一个极其微小的提醒。某位女士不断闪回的画面是这样:14年前,夏季,将近晚上9点,她从同学家,回自己的家,那时候刚好大学放暑假,她比较胆子大,于是在两条路中间,选了不该走的那一僻静小条。
就跟华容道似的,选哪条路很重要,大路远点,要绕一大圈,而从同学家到她家,中间有一条小河,不宽的人工河,用来给工厂排放废气的水,大概两米宽,哗哗哗地流动,水比较脏,叫它“小河沟”更恰当。左右两岸的斜坡,杂草丛生,大概半米左右的草。那是夏天,草已经很茂盛,间杂着,有一些树,树木种了两排,并不整齐。有的胳膊一样粗,有的再粗点,是些杨树。
这是发生性侵14年之后她的记忆。她不是一个擅长景物描述的人,但一切都不需去记住,因为那个被性侵的场面,从未离开。
她当时穿一件粉色的雪纺半袖衬衣,头发是短发,裤子是粉蓝色的长裤,没有背包。当时她看看大道,又看看小河沟两边的小道,选择了小路,这条近路大概有500米长。因为她之后再没去过那个地方,也无法丈量,估计是这个长度。她个子比较高,喜欢穿运动鞋,她以为快走几步,很快就通过这条没有灯光的小路,到达大路,能早点到家。她一边走一边寻思刚才跟同学聊天的话题,突然,她感觉到身后有人,然后,一把长二尺左右的刀,明晃晃地架在她脖子上,同时听到,“别动!”男人的声音,同时,她的左肩膀被狠狠地抠住,仿佛鹰爪嵌进肉里,总之,她被控制住了。
“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?!说!”男人的声音凶横,他喷出的气流和零星的口水,撞击着她领子上边的后脖颈,她颤抖着说,“知道。”她的声音不大,她不敢喊,她知道不能刺激一个手里有刀的人。
她事后反省过无数次,为什么要选那条路。同时也猜想,那男人到底藏哪儿了?因为草里蹲着人,不大可能。树后?但树木没那么粗壮。跟踪在她身后?她进入捷径之前,特意观察了一下,没人。难道他蹑手蹑脚地跟踪着?
这男人揪着她的胳膊,拉到一旁,低吼着让她脱衣服,他手里的刀离开了她的脖子,但依然举着,在半空。他劫持他的位置,恰好在捷径的中点左右,后面是一条大路,灯火辉煌,前面是一条大路,霓虹初上,很多车,很多人,但是远水救不了近渴。如果逃跑或呼喊,没等获救,她的脖子就断了。
审时度势是人的本能,她是一个人,她没哭没喊,哆嗦着脱衣服。她不是一个处女,知道面临的是什么,默默祈祷他的要求只是满足兽欲。祈祷,但不可以说出来,不能说出那三个字,别杀我。那好像是一种提醒似的。在那个斜坡上他脱了裤子,把刀放在他的右手脚边,这时她产生一个非常不理性的想法,去拿起刀,砍他。她飞快地评估了这个想法,放弃了。
出了状况,这个男人阳痿了。14年之后,男人的样貌还非常清晰地随时呼之即来,不呼之也来,他将近180的身高,大概少一两厘米,体重有135斤左右,偏瘦,穿着白色短袖衬衣,他郁闷地嘀咕一句,“他妈的太紧张了,以为又要杀一个人呢”,他的声音不大,像自言自语,也像说给被强奸者听,给他自己找点儿面子。哪怕强奸犯,也会因为阳痿而感觉没面子吧。
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他要她坐着跟他聊天,问问这,问问那,似乎在找寻一种比较正常的性关系的感觉。她非常恐惧,尽量配合着话题,大概7、8分钟,他可以了,然后性侵了她。他命令她穿衣服,她一步一步地按照这个拿刀男人的命令去做,听到穿衣服的命令,她知道,自己生存的希望比较大,因为死尸是不必穿衣服的。
想活,可以是一种耻辱,对于强奸案受害者,某些人是这样认为。这种感觉让她自贬为一只偷生的老鼠。如老鼠一样卑微地,等待下一个命令。这时那暴徒比刚才的情绪缓和些,因为没遭到什么反抗,一切很顺利,他得到满足。他又命令她把手表摘下来,那个一个亡故亲人的礼物,她很想请求那个强奸犯,别拿走。想想,算了,给他手表,之后是钱,她没带多少钱,20多块。总之,除了命,她什么都被剥夺了。
强奸是一种剥夺,抢劫也是一种剥夺,肉体,尊严,金钱,然后是……未来。
强奸犯中的一部分人,希望剥夺受害者的未来,于是他们提“下一次”。哪怕下一次子虚乌有,他也想说说。他趁着朦胧的月光端详她的脸,看了几秒说,“下一次……”她的心脏砰砰地跳起来,脑里快速地盘算,他用什么来控制着发生这样的下一次?
他说,“下一次,你这个手指戴一个戒指,给我看。”
这是本案受害者一直没想明白的话,14年也没想明白,这么无厘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她没答应也没反驳。也许是从强奸犯自己生活中的某个场景而来,跟她没什么关系。这时他果断地说,往前走!别回头!
他拎着刀,她往前走,她不敢跑,快速地走。她不知道他会不会从后边砍过来一刀,她感觉后背凉飕飕的,因为随时有一刀砍过来,200多米的距离,如芒在背地走了不知道多久。快了快了,她终于到了路口,到了亮处,她撒腿跑了出来,跑到车水马龙的街道上,她大口喘气,看着来往的车辆和遛弯的男男女女,她想说,你们知道吗!我差点死掉!我遇到一个拿刀的男人,他袭击了我!强奸了我!
她知道跟这些人无关,即便大家跑过去,那人一定早已不见踪影,他命令她“一直走,别回头”之后,就会从另一个方向逃掉,尽管她没回头看,但事情肯定是这样的。多么猥琐的一幕。
她盘算报警问题。她知道有这个义务,这个人渣可能还会采取这个方式,继续作案。她挣扎着,然后说服了自己,没有报警。
她没报警。没有。跟大部分的性侵受害者一样。她没告诉父母,跟大多数的性侵受害者一样。父亲发现了她的异常,问怎么了。她想办法遮掩过去,父亲问她,为什么你总愣神?她也一次次地遮掩过去。
现在是自己被强奸,告诉父母,就是一家子被强奸了。这是性侵受害者都懂得的道理。并且,第一个问题肯定是:你为什么要走哪条僻静的路,你脑子进水了?!
她也知道自己错了,选错了路,何必再去责备呢?但亲人,或者外人,都从这些角度出发,去责备受害者。他们是带着好意,意思是:如果你不走那条路,就不会被如何如何了。我心疼你。
不能告诉家人。一旦告诉,他们永远停留在“知晓”这个状态,永永远远回不到他们“不知晓”那个状态。告诉父母,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选择,无法修复。你在父母眼里,就一直是个强奸案受害者,直到他们死,或你死。如果你怎么样了,他们立刻会说因为那次强奸。总之,告诉父母很啰嗦。大家减少一个彼此折磨的重大材料吧。不告诉。
这件事也对她与男朋友的关系产生影响,男朋友的身材与那人大致相似,会突然不经意地感觉,男朋友是那个强奸犯,尤其是看不到他脸的某个刹那。她的心会一惊。后来终于分手了,她也逐渐将兴趣放在个子矮一些的男性身上。这个兴趣的改变,原来并不为显意识所知,是多年之后,她才恍然大悟,为什么对高个子男生失去了兴趣。之前一直是潜意识在作怪。总之,改变一个人太多太多。
她觉得自己是只老鼠,又脏又臭,又猥琐,还记得当时丛林里刷拉刷拉的蛐蛐叫声。地面也很脏。好在没谁知道,她可以假装这事从没发生过,有时回想,会厌恶,有时回想,会心情平静,但画面总是非常清晰。她也猜测,后来那个强奸犯怎样了。是不是改好了?是不是作案的时候被人自卫弄死了?是不是被警察击毙了?是不是被抓住判刑或枪毙了?是不是突然得病自然死亡了?他当时说,“我还以为又要杀一个人呢”如果不是撒谎,是前科累累的一个人,他会自责吗?会不会哪天吊死在一棵树上?
她当然自责,因为没报案。如果有人劝她报案,她会说,“去她么的正义吧,我还想尽量正常地活下去!”
报案之后,可能会正常起来,可能会更不正常。但不告诉外人,不报案,可以假装正常。画面闪回,随时,三天一次,五天一次。幸运的话,一个月甚至半年也不闪回。当然,她有时候愤怒地想用刀砍死他,他对她像一块擦脚布一样,抓过来随意凌辱。可惜她不能,不能做任何事情去惩罚他,很无能为力。
假装正常地活着,跟死亡的区别到底有多大,那些自杀的性侵受害者最清楚。


 主页 > 两性生活 >
主页 > 两性生活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