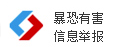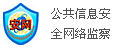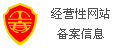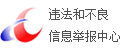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我的头越来越极重,眼睛也不断地斗殴。高速走了30公里阁下,出租车溘然从中间阶梯飘到了超车道,我吓了一跳,赶忙将偏向打了返来。
几个男孩也随着惊叫起来,坐在副驾驶的男孩心有余悸地说:“喂!师傅,不想拉我们也不消这样吓我们吧?”后排一个胖乎乎的男孩伸过甚来:“喂!适才你那招漂移太刺激了,我喜欢!再来一个!”
我对他们说不是存心吓他们,也不是什么漂移,真的是我生病了,头晕得很。
“真生病了啊?那你赶忙让我们下车啊!”坐副驾驶的男孩搬弄地说,后头的几个也就随着闹:“对啊!赶忙让我们下车。吓死宝宝了,我的小心脏啊!”
我知道他们是在存心气我。高速路上下客,情节可比拒载严重得多。
可是徐徐地,他们都不措辞了。因为,尽量我很是尽力节制本身,但适才那种“漂移”越来越多。后排一个男孩开腔了:“喂,师傅,你真伤风了哇?”我点颔首。
“能撑得住吗?要不让我来开?”我没答复,也没规划让他来开。可我的头越来越眩晕,持续跑了好几个“S”型,吓得几小我私家连连惊叫。
“喂!师傅,我拿了驾照一年多了。真的,不可你看看?”适才谁人男孩把驾照递过来。想着离重庆城区尚有100多公里,还要开一个多小时。我心一横,把车停在路边,换了后头谁人男孩来开。
开始的时候,我还担忧小伙子开车技能不可,尽力让本身不睡已往。可是徐徐地,我的意识越来越含糊。
迷模糊糊中,我听见有人说:“仿佛真的发热了,好烫。”“我摸摸。”一只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。“真发热了!”我昏睡了已往。
醒来的时候,我已经在医院了。输液架上挂了3个空瓶子,尚有2个小输液瓶在等着列队。阳光可贵地照进来,撒了一房子金光,很是暖和。
|


 主页 > 口述实录 >
主页 > 口述实录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