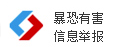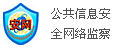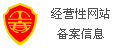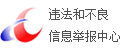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唐诺兰见我醒来,冷哼了一声,“唐言,你说你怎么不直接死了?”
扫了她一眼,我淡然道,“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

她不愉快 ,自然不会给我好脸色,“你在餐厅里晕倒,牧深将你送来的,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?”
我失笑,讥讽 道,“原来是打搅 了你们约会,抱歉 。”
她自然能听出我话里的讥讽 ,冷哼一声便出去了。
进来的是严牧深,男人双手抄兜,冷冽淡薄 ,修长如玉的身子立在病床头,漆黑如夜的黑眸看着我,一动不动的。
他不开口,我心里有些发毛,主动开了口,“你今天不出差么?”
昨晚他似乎说过,要出差。
“我没去,你很失望?”他心情不要,话里就能听出来了。
他的目光太晦暗难测了,移开目光不和他对视,我开口,“你送我来医院的?”
“你希望是谁?严牧函?照样 你其余 情人?”
压下心里的不悦,看向他,我开口,“严牧深,我们之间的事,一定要扯上牧函么?你和我妈之间,我说什么了么?”
他不开口了,走向我,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,抬眸看了看输液的瓶子,最后将目光落在我身上,“我和你妈从一开始就没什么。”
我愣了一下,这是解释?
“你们之间的事情,我没兴趣知道。”我是真的没心情知道,所有的事情乱成一团,这些事,剪赓续 理还乱。
病房里太过宁静 ,我知道他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怒意,若不是因为我此时躺在病床上,恐怕他会发生发火 。
但最后,他只是看着我,无声叹了口气,开口道,“疼么?”
我:“”
“还好!”
这样突然随和,让我不适。
他几弗成 闻的冷哼了一声,却是 明显的注解 自己生气了,“疼点好,不长记性的下场。”
我
这人怎么了?
空气里就这么缄默 了。
严牧深给我解决 了住院手续,支配了我的事之后,就一直坐在病房里守着我。
其实不是什么大病,就是简单的食物过敏。
我一直没见到严牧函,病房里没有旁人,弗成 能问他的去处,索性也就不开口了。
到了黄昏 ,严牧深起身出了病房,我才给严牧函打了德律风 。
德律风 响了两声,那头便接听了,“言言,你怎么样了?”
“没事!”应了他一声,我道,“严牧深没找你麻烦吧?”
他似乎有些自责,开口道,“没有,抱歉 ,我不知道粥里加了虾仁,是我大意了。”
我摇头,意识到德律风 那头看不到,便道,“怪不到你头上,我没什么大事,你现在既然已经回费城了,有什么盘算 么?”
他静默了一会,开口道,“言言,我唯一的盘算 是带你离开”
“严牧函,我已经嫁给你哥了,”打断他的话,我蹙眉开口。
“你爱他?”
我缄默 了,他开口道,“言言,我迟早会将你抢回来的。”
“牧函”
话未曾出口,德律风 已经被抽走,我愣住,回头,对上严牧函阴冷冰寒的黑眸。
“唐言。”他看着我,黑眸里布满了冷冽,“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,你是不是特别有造诣 感?”
男人低冷沉郁的声音里泛着一层轻薄的自嘲,他扶着我的肩膀,完完全全的面对着我,眼神非分特别 阴郁。
|


 主页 > 另类小说 >
主页 > 另类小说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