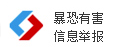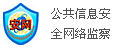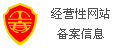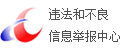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那么床上的那个是?
陈簌楼蹲下身子,俯视着爬在地上的褚凰儿,修长的手指捏起褚凰儿的下巴,冰凉的指间摩挲着她右边脸颊的刀疤:“啧啧啧,你比你姐姐更烈,居然要咬舌自尽。”
褚凰儿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,意识也越来越模糊。
只见陈簌楼面色一紧,看向床上的光景大步走去,质问道:“你把他怎么了?”
就在意识消失之前,褚凰儿就这陈簌楼的灯光清楚的看到,床上那个、刚才被自己一针毙命的,居然是他的父亲,陈中……
虽然褚凰儿已经想到床上那个不是陈簌楼,但是怎么也没有料到,对她欲行不轨之事的人,竟然是自己名义上的公爹!
这又是怎么一回事?儿子无能,父亲取而代之吗?
此时此刻褚凰儿看着仇人就在自己的眼前,心中愤懑不已。

奈何自己仅残存一丝意识,身体已完全被燥热吞并,瘙痒难耐。
看着眼前的陈簌楼,口中竟下意识的发出羞人的声音。
陈簌楼已在床榻上发现了那支发簪,放在鼻子上嗅了嗅,眉头紧蹙。
他闻声走到褚凰儿的身边,捏开她的嘴看了看伤处。
断舌之痛牵动着全身,可刺痛之下,陈簌楼手指的冰凉却让褚凰儿心头微颤,越发挑起了她身下的反应。
残存的意识恨不能让褚凰儿索性咬断舌头死了算了,可是陈簌楼却紧紧捏着她的下巴,动弹不得。
只见陈簌楼邪魅一笑:“姑娘,你说我是先救你上面好呢,还是这下面……”
陈簌楼目光扫过褚凰儿的身体,刚才她的层层嫁衣已被陈中扒开,只剩一件遮羞底衣挂在胸前。
褚凰儿绝望的昏了过去,闭眼之时,一行清泪划过面颊,划过伤疤,落在陈簌楼的指腹之上。
陈簌楼垂眸看着褚凰儿,回想起,那日明月之下,同样是这张脸,同样身穿大红嫁衣,却多了几分柔情。
她站在井边,望着天上星辰,又回头看向陈簌楼,浅浅一笑:“求你带给我妹妹一句话,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”
说罢便一跃而下,荡起水波,久久不能平静。
那日的月色是真的好啊,不像今天,阴云密布。
陈簌楼无奈摇摇头,抱起褚凰儿,向墙壁上挂的一幅画走去,同时口中发出一声鸟叫。
不久之后,从屋外走进一紫衣女人,看到屋内的情景,“公子,这是怎么一回事?”
陈簌楼用脚尖顶了顶画正对的地砖,一个暗门从画边打开。
声音冷的如刀刃一般:“找一个破了身的丫鬟,杀了,然后和陈中放在一起,把这里烧了。”
他看着怀中的褚凰儿额头已沁出薄汗,身子烫的和火炉一样,冷笑道:“在那个丫鬟上的右边脸颊上划一刀子,记住,一定是活着的时候生划。”
说罢,陈簌楼抱着身中情药的褚凰儿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
褚凰儿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女工,她静不下这个心去缠丝绕线。
可褚凰儿最喜欢做的又是女工。
每当阿娘从绣房接下零活,她就会和阿姐坐在家门口的那株凤凰树下,一边绣着帕子,一边说悄悄话。
尤其是凤凰花开的时候,风起花落,衬着两姐妹的罗裙,比那朝霞还要娇艳。
“阿姐,阿娘说等我们过完十五岁生辰后,就让媒婆给我们说亲,你说我们未来的夫婿会是什么样子的?”
“那阿姐问问你,你想要嫁给什么样的夫君?”
褚凰儿立即放下手中绣的锦帕,一手叉腰,一手在风中挥舞着:“我褚凰儿要嫁的,定是那征战沙场的好男儿,横枪跃马,威风凛凛,我绝对不要文绉绉的柔弱书生,扭扭捏捏的,像个娘儿们。”
褚凤儿掩面一笑:“姑娘家家的,还笑话人家书生,书生不好么,闲来时,与你花前月下,饮酒作赋,岂不美哉。”
褚凰儿闻言,眼珠子一转:“他们都说陈家的那个陈簌楼就是个难得的才子,三岁背诗,七岁做赋,样貌啊比那姑娘都俊秀,阿姐,你要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人啊!”
“呸呸呸,不许胡说,他都娶了六房夫人了,阿姐给你说,哪怕穷,哪怕苦,也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”
“那我们两个嫁同一个人好不好,这样我就能永远跟阿姐在一起了。”
褚凤儿也放下手中绣了一半的帕子,握住褚凰儿的手:“虽然你只比我晚落地半柱香,可你离知晓人事还差很多,你要记住,这个世上可以分享很多东西,唯有感情,只能独你一份。”
褚凰儿不解,却也不悦,撇了撇嘴坐回原处。
她看到阿姐绣的又是鸳鸯戏水,鸳已经绣好了,可那只鸯迟迟没有下针。
而自己的傲雪寒梅,虽不及阿姐的传神,但却是针针果断,傲气凌人。
阿娘总说她秀的寒梅太过孤傲,总感觉差点什么。
可褚凰儿才不在乎差什么,只要能给家里换来钱就行。
褚凰儿还想问问阿姐,独一份的感情是什么意思。
可等她扭头时,不知怎么,凤凰树下多了一口井。
只见阿姐身披大红嫁衣,决绝的一跃而下。
|


 主页 > 另类小说 >
主页 > 另类小说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