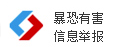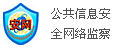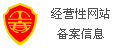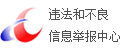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而且,多年下来,我还得出了一个鲜少有人知道的经验:新皮鞋买回的头十天,天天给它刷一次油,以后会容易打理很多。
多数情况下,就拿个纸巾擦擦,它也锃亮锃亮的。
女儿今年二十五了,也有了结婚的对象。
这么多年的白天和黑夜,仿佛就像是一场梦,“倏”地就过去了。
短暂的发愣后,我发现自己并无什么异常,立马起身洗漱好,骑着我的小电车往上班的地方冲去。
只是,一路上我总会想起陈墨那不曾回头的离开,和冰冷的关门声,心下没来由地涌出一种孤独和失落来。
如果今天早上我一直不能动,会怎样?

这种略带无奈和绝望的感觉,在远远听到孩子们的叽喳声时,都消失不见了。
陈墨对我这工作一直是嗤之以鼻。
说工资老低不说,整天和一帮毫无营养的孩子打交道,成天伺候他们屎尿屁,做一辈子都是老样子。
可我喜欢,孩子们的心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地方。
他们饿了就吃,困了就睡,没有一丝掺假,还有什么比他们更纯更真?
而且,和他们在一起时,时间是最容易流逝的。
一晃半个月又过去了,这天的下班时分,孩子们都走得差不多了,只剩十来个全托的,也由值班老师带着在做游戏。
我拿上包包,找出电车钥匙,准备下班。
只是,没等我和同事开口打招呼,之前那怪异的头疼感觉又来了。
我想伸手去抱头,却发现自己已无能为力。
只能任由身子重重地跌落在地板上,一声尖叫声响起后,三三两两的人很快围了过来:“周老师!周老师你怎么了?”
我能感知到她们的呼唤,却无法回应。
很快,有人脱下我的鞋,使劲按摩我的脚趾头,掐脚踝处的穴位,还有人在掐我的人中。
这次,没等我自我恢复,我就被送到了医院。
等我清醒过来把两次发病经过和医生讲了后,医生告诉我说,这很可能是轻中风,更极有可能是出血性脑中风的前兆。
那一瞬间,我傻了。

我脑海中全是形形色色的、我见过的中过风的人,有拄着拐杖蹒跚前行的老太太,有坐轮椅上歪嘴斜舌淌着口水的老头,还有瘫痪在床完全不能自理的活死人……
我完全不能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变成他们中的一员,我也绝对不能成为他们。
因为,我瘫在床上不能动弹不能言语时连个发现的人也没有。
可是,医生的话又字字句句、铿锵有力,让我不得不面对这种可能。
如果我再不重视,极有可能就变会成他们那样,甚至更严重。
医生见我醒后没多大问题,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后,开了点药。
我也实在受不了医院那压抑的氛围,拿了药就回家了。
晚上十点多,陈墨回家时,我起了几次念,想和他说说白天的事,他却洗完澡就抱着手提电脑进了书房。
好不容易等他回了床上,我还没说完,他就背对着我发出了轻微的鼾声,临睡前咕哝着:“现在不是没事嘛,按时吃药吧……”
|


 主页 > 两性生活 >
主页 > 两性生活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