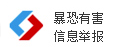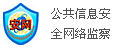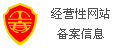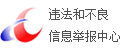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这种患得患失的日子,让我的血压受不了了。
血压直拗地升高,我时而会头晕。
自认为身体很棒的我并没在意。
难受时我扔嘴里两片降压药,不难受时我该干啥干啥。
那日我又难受了,英霞回来了,我看下日历,后天是开资的日子。
这次难受的厉害,头胀的很。好象有什么预感,我决定上医院看下。
英霞撇着嘴,说我小题大作。

我准备出门,英霞说再挺两天,观察一下再说。
我不理,执意要走。
英霞就背着包跟我出来。
我大喜,关键时刻,表现还不错。
到了车站,英霞上了另一辆去她自己家的车。
我看了她一眼,随着关车门的一声“啪”,我听见了我的心碎裂一地的声音。
我一个人孤单单来到了医院。
一项项化验后,医生凝重的脸色,让我感到问题的严重。
医生告诉我,我的心脑血管大面积被堵,必须住院,特别是脑部,堵的很重,随时有脑梗的可能。
我给英霞打了电话,人家告诉我:“别听医生的,医院都为了挣钱,吓唬人的。”
我说必须住院,求她来护理我几天。
英霞说她工作忙,离不开。然后,不等我说下文,就挂了电话。
没办法,我只得打电话告诉我的儿子女儿。
一个小时后,我的儿女从不同方向,开车过来了。
同行的还有泪眼模糊的前妻。
不知是太懊悔,也不知太激动,我一下子昏了过去。
等我醒来时,我发现我躺在医院急救室。
隔着厚厚的玻璃窗,女儿告诉我,我己经昏睡了二天二夜,头部於血已手术清除,暂时沒生命危险。”
由于我心脑同时堵塞,给医生治疗带来很大困扰,因为有些药物不能同时服用。
靠着我体质不错和要活下去的意念,再加上医生护士的倾心治疗,有些功能开始恢复,我也能吃些流食了。
医生建议我回家休养,希望会有奇迹发生。
住院期间,儿女轮班护理,前妻也隔三岔五来探望。
而英霞只打了一个电话,问我记不记得打玉米人的电话。
至于病情,象征性问了一嘴,不等这边回答,就迅速挂了电话。
出院后,依旧是儿女请了假,轮流黑天白天的护理我。
大概回家一周左右,英霞来了。
她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,确定我大小便不能自理,以后恢复希望不大,当时就提出了离婚。
我早已看透,万念俱灰,一口应了下来。
也许我身体底子太好,再加上儿女侍候的精心,还有前妻的关心和鼓励,当初死马当活马医的我,竟然神奇地一点点好了起来。
从能动,到能坐,又能站,现在可以扶着轮椅慢慢行走了。
我让儿女去忙各自的工作,自己雇了个白班保姆。
现在,村里动迁了,我将分到一笔不菲的拆迁款。
英霞听说后,来找过我两次,希望能复婚。
我对她早已看透,再无半点留恋,自是严辞拒绝。
前妻随儿女经常回来,洗洗涮涮,做些我爱吃的饭菜。
儿女话里话外有意让我们复合。
我俩都沉默了。
我知道,今生我们回不去了,我曾经那么残忍地伤害过她。
余生,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活,我的动迁款,将分成二份。
一份给儿女,一份给我的前妻。
|


 主页 > 两性生活 >
主页 > 两性生活 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