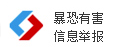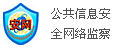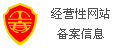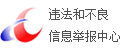|
美满的生活只过了半年,这天,是大年二十九。
我收到消息,胡军出事了。
我去到胡军家,小土房围着里三圈外三圈的人,屋内几个妇女陪姐姐待着,姐姐抱着心铃,娘俩哭得几次昏死过去。
我从别人口中得知,胡军今日在工地上,因为建材质量不过关,胡军从十二楼坠下,送到医院后,医生直接下了死亡判决书。
姐姐意识恍惚着,什么也问不出,什么都干不了,只我和胡军的几个工友操持着后事。
胡军出殡前,姐姐就单独陪着他,坐着个小板凳,目光空洞,陪着他说话。
到了出殡那日,姐姐一个人,压在棺材上,不让任何人靠近。
心铃冲上去喊妈妈,姐姐连她都不认。
双眼充斥着血丝,有人上去拉开她,她抓起人胳膊就咬,几近癫狂。
终于我和几个男人合力控制住她,一颗颗钉子封住棺材,姐姐一声痛哭:“胡军啊!你就这么不要我啦!”
嗓音凄厉,天空昏暗。
那个重新带给她希望的男人,天使般降临,天使般离开。
那年,姐姐才二十九岁,可那缕缕白发和世事在脸上留下的深阖痕迹,如岁月般可怖。
我让姐姐回家住,孤儿寡母独自生活实在不易,可姐姐不愿,她说,她可是老胡家的儿媳妇儿。
姐姐再没找,也有上门介绍合适的,可姐姐都是一句话回绝:“我命硬克夫,也别再害了好人家了吧。”
久而久之,也再没人上门了,姐姐靠着一双手出大力,养活着自己和心铃。
心铃实在争气,从上学开始成绩就好,姐姐每次和别人提起这个女娃子,眼角满满的都是笑。
心铃真的是撑着姐姐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
我随着父母的愿,父母命,媒妁言,娶妻生子,平平无常。
可姐姐,却是我心中无法触及的痛。
心铃上了大学,离开了家,留下姐姐独自守着小土房。
我常常去探望,见着她无数次对着墙上胡军遗像述说着生活琐事,她和心铃的近况。
心铃结婚那日,要给姐姐好好打扮一番,心铃笑呵呵地对姐姐说,可不能输给婆婆,可姐姐说,什么都不用。
姐姐又一次穿上了和胡军领证那日穿的红裙子。
新郎来接新娘子出门,心铃走了两步,突然转身跪下,给姐姐磕了个头:“妈!”
姐姐上前拂去心铃脸上的泪,声音哽咽:“娃儿听话,妈希望你永远幸福!”
姐姐目送着心铃离开,浑浊的眼中,泪无声地流。
从胡军走后,姐姐已经很久,很久没有哭过了。
姐姐直直地看着车的方向:“闺女嫁人了,他也该放心了。”
我一生平澹,无大起,无大落,只因为小时候的一次贪玩,给我最爱的人带去了无法弥补的伤害。
我尽可能地赎罪,亦愿天下人,普通平凡,得偿所愿
|


 主页 > 口述实录 >
主页 > 口述实录 >